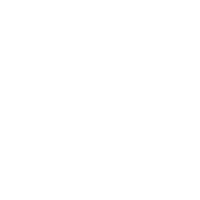近日,叶锦添携新书《凝望:我的摄影与人生》分别在广州和深圳举办了两场读者分享会,与大家分享艺术人生及“东方诗意”的DNA。
叶锦添精选出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摄影作品109幅,并配以亲切的回忆性文字,在今年春天出版了首部自传性摄影随笔集——《凝望:我的摄影与人生》。书中,叶锦添以摄影为媒介,将自己独特的摄影美学主张和人生经历娓娓道来。这位电影《卧虎藏龙》背后的男人,戴一顶鸭舌帽,举止儒雅,说话轻声细语,就如同在广州街头偶遇的一位阿伯。结束广州方所新书分享会后,叶锦添接受了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的采访。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波
关于叶锦添
多年来,叶锦添一直活跃于电影和艺术界。作为在电影与舞台艺术指导、服装设计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视觉艺术家,叶锦添曾凭借电影《卧虎藏龙》一举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艺术指导”。而自1986年参与第一部电影《英雄本色》起,他担任过多部电影、戏剧的美术指导与服装设计,包括2023年备受关注的《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叶锦添透露,他的艺术创作并非仅限于电影与舞台艺术,他中意的身份是“摄影师”。叶锦添在大学学的是实用摄影高级摄影专业,属于科班出身。在过去的近40年里,无论是在电影拍摄现场还是在旅行中,叶锦添一直在用镜头捕捉电影的珍贵时刻,并传达自己对世界的独到认识与探索。
叶锦添坦诚地对读者分享会上的观众说:“我时常会感到自己处于瓶颈中,会有自我重复的感觉,于是经常在服装、摄影、电影之间跳来跳去。”
关于新书
“凝望”有非常丰富的含义
广州日报:您怎样定义自己?
叶锦添:我自己是一个多面体。比如我做舞台,也是各种不同的舞台,有大舞台、歌剧、小型舞台,电影也是一样。自己最重要的特色是多维,向着多维的方向不断发展。对我现在来讲,我不太计较我是美术指导还是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认识最新的朋友,打破我自己的限制。
我的性格其实也不太像服装设计师,我的穿衣风格从来没有变。我很两极,有时候很希望出尽风头,有时候又希望最好大家不要看到我。
广州日报:这本书的副书名是“我的摄影与人生”,主书名是“凝望”,作为自己纯粹意义上的第一本摄影集,您怎么确定这本书的书名?
叶锦添:跟我哥哥有关,小时候他教我摄影。哥哥教我一个东西,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怎么注意人的眼神,“凝望”有非常丰富的含义。
我曾看到一个小孩的眼睛,就拍了下来,拍完之后我问自己,小孩给我的感觉是我赋予他的,还是他给我的?后来我去到其他地方,又拍了非常多小孩的眼神。他们看你的眼神,不是简单的开心或不开心,摄影最珍贵的是你在现场,你不是在虚构的地方去拍摄,你是在一个真实的空间拍照片,所以拍的是所有东西。用“凝望”做标题,内涵在于:不管是胶片里的那个人在凝望我,还是我自己藏在胶片的反面去凝望,你会发觉你在想什么、你在干什么、你要表达什么,全都在这两个字的意境里。
关于摄影
摄影就是个人心灵世界的展现
广州日报:新书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很长,您是怎样考虑的?
叶锦添:我们同时在一个空间里,每个人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而摄影就是个人的心灵世界的展现,很多人可以用文字或者用别的手法,但摄影很及时,有些场景过去就没有了,所以它的美妙性就在于它的这种独一无二。
开始摄影创作的时候,可能是我碰到的人很特别,他身上有很特殊的东西,吸引我去创造一种可能性。后来,我没有看到能那么吸引我的人,所以我没办法聚焦在某些人身上,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我一直在拍艺术家,所以后来特别喜欢拍一些真正旅途上遇到的事物,这是我选择作品的考虑。
广州日报:能否向读者分享一下作品《三个女人的故事》?
叶锦添:这张是早期的作品,我运用了暗房技术,将两张照片拼接在一起,呈现出张曼玉独有的气质魅力。
当时拍摄的时候,她在纽约的一栋房子里面拍戏。这其实是两张照片,当时几乎只用了两秒钟就拍下来,之后就没有机会再拍了。因为她当时还没有很红,拍完《人在纽约》这部戏,她拿了自己的第一个最佳女主角奖。
广州日报:这里看到的是两个时间点的张曼玉,作品叫《三个女人的故事》,第三个女人在哪里?
叶锦添:没有,“三个女人”并不是三个张曼玉头像。
这张照片经常被用来做海报。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就是多维,我一直在追求非单维的世界。多维的世界没法描述,几乎你讲的一句话已经在抵消下一个可能性的逻辑,下一个可能性的逻辑如果确定的话,第一个逻辑又开始动摇,所以你一定要在一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去接受它。具有这种能力,才能开启多维世界的思维,所以我把这个作品命名为《三个女人的故事》。
关于生活
没时间见朋友 摄影是自我对话
广州日报:读者看这些文字和摄影作品,会产生很多思考,例如您在生活中是不是一个善于沟通的人?
叶锦添:真正能跟我沟通的人不是很多,我工作的强度很大,经常都在处理很麻烦的事情,要管好多人,要管很多创作,要解决好多问题。生活中相处的都是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看到我都怕了,所以我常常没有太多可以对话的对象。
其实,我聊得来的朋友很多,但是没时间去见他们。所以摄影也是一种自我对话的方法,我也很喜欢写东西来自我对话。我不是有目的地想拍什么东西,而是在自我的对谈里面,慢慢产生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我一个人观察很复杂或者很简单的事情,慢慢渗透出我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美感或者是你们刚刚谈到的对现实的关怀。
广州日报:您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这么长的艺术人生中,在创作上有没有明确的转变轨迹?
叶锦添:早期我觉得构图很重要,每张照片的构图力求完美,早期的那些黑白照片都是属于这一路的。接下来,我开始在影楼里面尝试服装摄影。之后,是拿着“傻瓜机”到处拍,不再追求构图,拍出很多很有趣的、想象不到的东西,这或许算是转轨。
我目前做的电影、作品都是根据非真实性的记录而进行创作的。说到转变轨迹,那我会不会回到非虚构的古典里面?会的,有一天我会回到古典。
广州日报:早期您从摄影开始慢慢进入电影,进入舞台美术,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摄影在您的人生中有什么样的地位?
叶锦添:当时我参加了一个绘画比赛,有三项大奖,我拿了两项冠军。那时候徐克注意到我,我有机会参与到电影《英雄本色》里。
有时候,我在电影领域走不下去,就开始转向舞台创作;在舞台走不下去的时候,又回到电影。
当时我觉得很难有人投资拍我想拍的电影,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痛苦的等待,我有机会认识了舞者吴兴国,帮他一起做《楼兰女》,那时候应该算是一鸣惊人。
现实生活中,我曾经对摄影很绝望,不知道它能做什么。我后来很幸运,当我做电影的时候,发觉摄影不只是为了记录,我发现了时间的深度和意义,但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结果——摄影能指向未来,它虽然在形式上进行记录,但其实它在创造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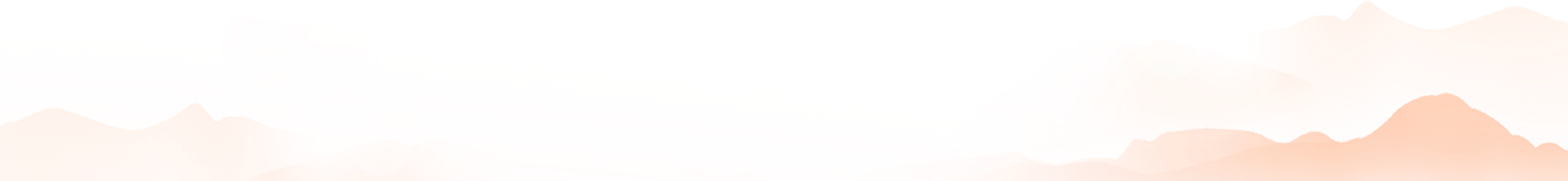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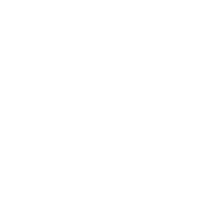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