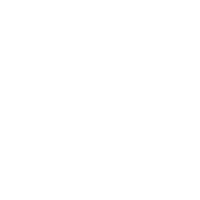雪花像得到一道神秘的指令,在寒风的陪伴下,如赴约一般,接踵而至,一场又一场,亲吻辽阔的北方大地。
白雪飘飘。田野、村庄、道路、房屋、街道、农家的小院儿,都被白雪覆盖。天地间,银装素裹,粉雕玉砌,好一个美丽纯洁的世界。放眼四顾,北方大地就像一幅展开的逶迤壮美的画卷,身在其中,人就像一粒小小的尘埃,不由得心生敬畏。
唐代诗人刘长卿曾于风雪之夜欣然写下“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的诗句,虽寥寥数语,却如同简笔画一样,简洁传神地勾勒出一幅雪后苍凉的图景。每每咀嚼,总有千年馨香,如丝如缕,盘桓心头,久久不散。
我是在北方乡村长大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住的都是低矮的土坯房。早在寒风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启程之时,乡亲们就要“披房”。何谓披房,即给房子做保温,就是将农作物莜麦秸秆的碎屑均匀地铺在房顶上,再铺一层胡麻的秸秆,最后再压上石头,以防被呼啸的寒风卷走。
为什么一定是胡麻的秸秆呢?因为小麦的秸秆光滑,互不粘连,石头都无法使它们降伏。当西北风嘶吼起来的时候,它们热烈地回应着风,心甘情愿地追随着风的脚步而去。而胡麻的秸秆互相牵绊,如同一张绵绵密密的大网罩住了房顶,再加上有石块加持,几无被风卷跑的可能。多年之后,读到大诗人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时,我不禁佩服乡人的智慧。
最妙的是落雪之后,到处是白雪皑皑,站到院子里,再也看不见对面屋顶上褐红色的“披房柴”,而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洁白棉被。那一座座低矮的房子,如同一个个白色的大面包。这意味着最严寒的日子来了。乡亲们也不急,生活切换到了慢进键,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木柴在炉膛里发出快乐的吟唱,仿佛在大声而高调地说着什么热烈缠绵的情话,让炉壁听到后羞红了脸。人们围炉而坐,煮一壶奶茶,或烹一锅美食,任茶香、奶香、肉香、菜香氤氲,弥漫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也渗透到人们的每一个毛孔中。乡亲们的脸上也终日荡漾着满足欣慰的微笑。光阴轻缓,日子安暖,夫复何求?
日复一日,严寒像一把大锁,锁住了这里的一切。“春种秋收,夏耘冬藏”,人们在这严寒最盛的季节里,停下忙碌的脚步,安静地品尝美食,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生活的馈赠,也是大自然的美意。
而雪,又何尝不是大自然对人的恩赐呢?看,那一个个憨态可掬的雪人,一个个雪球在空中飞舞,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在街道上响起,都是雪给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带来无穷的乐趣。雪让一个个大人变成了孩子,让每一个孩子变成了天使。啊,浪漫温情的雪。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几十年的光阴倏忽而过,我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被时光的飓风裹挟,飘零他乡,在异乡的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扎下根来。每到寒冬,我是多么怀念童年生活,怀念“天寒白屋贫”的雪后美景。
(张燕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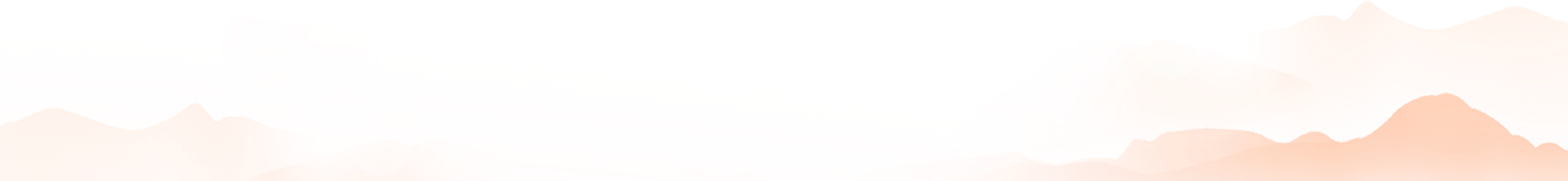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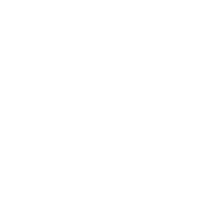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