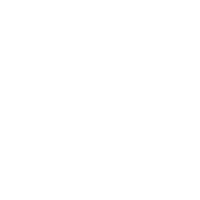一位山西老人崔玉岐在退休后带着父亲的遗愿,开始寻找当年在战争中牺牲的“三叔”。“三叔”名叫崔海治,1947年1月在汾孝战役中负重伤,送院救治后无果,牺牲时年仅23岁。今年,在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及其团队的帮助下,确认了山西吕梁南村烈士墓编号为M19的遗骸就是崔海治烈士。
从2015年远赴缅甸密支那为中国远征军烈士寻亲开始,文少卿和团队至今已经采集了10个战争遗址中的1000多具“疑似”烈士遗骸的样本。他介绍,现有的“法医考古”手段除了能通过较为完整的面部颅骨恢复烈士的“容貌”外,还能够通过基因组学、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同位素研究等学科交叉研究,进一步还原烈士生前的种种经历,提供更多“档案”,最终为这些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们找到亲人。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除署名外)
今年9月30日,复旦大学校内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该展览以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村革命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项目为基础,通过发掘过程、DNA寻亲、烈士死因、复原照片、个体生活史等信息复原呈现的方式讲述英烈故事,传承烈士精神。
“在这个展览上我看到很多的留言,很感人。”文少卿回忆,“当晚我过去看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老人正在给怀抱中的小孩认真地讲过去的故事。由长辈告诉晚辈当年这些人为什么会挺身而出,现在的和平生活是如何来的,我觉得非常重要。”
帮远征军烈士寻亲
呼吁建立“双DNA”数据库
2015年,文少卿在经常合作的西北大学教师陈靓的朋友圈看到一条帮中国远征军烈士遗骸寻亲的信息。文少卿回忆,那一年,缅甸密支那中国远征军的墓地上要建设一所小学的厕所,海外华人把消息传入国内后大家积极沟通,想把烈士遗骸收殓回国。“我觉得我们能够办到,就接了下来。”
文少卿解释,由于远征军遗骸在当地高温潮湿的条件下会高度降解、高度损伤,应用传统法医学的方法寻亲是很难的。“传统法医学依靠的是STR基因检测技术,STR遗传标记DNA的片段一般长度都会大于100bp。但像缅甸密支那等南方地区,能够提取到的样本长度则是远低于这个片段长度的,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了全新的方案来为远征军遗骸寻亲,其中也进行了一些科技创新。” 他介绍,通过现在的算法,在提取到DNA片段、捕获富集一百多万个SNP遗传标记后,能够比较准确地寻找到三级以内的亲属,而在五级以内的亲属则是“可以试一试”。“毕竟五级之后就已经出了五服了。”
通过DNA鉴定,文少卿发现远征军遗骸生前大多来自云贵川等中国西南地区,他们也将检测结果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同时呼吁亲属前来寻亲。“若只是单方面的寻找,无论是为烈士寻找亲人还是亲人寻找烈士,都是很困难的。”文少卿说,因此不但要建立“疑似”烈士遗骸DNA数据库,同样要建立“疑似”烈士家属的DNA数据库,两者进行实时比对是可行性最高的办法。
最少半边面部颅骨
可复原烈士“面容”
“当你所做的遗传位点越多,就越能够满足各种复杂关系的判定。”文少卿举例,如人们常听说的“亲子鉴定”,由于是一级亲人关系,往往需要20多个位点就足够了。“传统法医学的位点数量大概在几十个,但是当级数越多,需要的遗传位点数量就要翻番了,而且如果烈士遗骸的样本是高度降解的,很多位点还不一定能够测出,就要给出足够的位点数量‘空间’,如今最高已经能够达到124万个位点,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他告诉记者,如今根据DNA的数据进行复原,一种是没有任何参照直接画像,准确率仅能达到70%;另一种是有参照物,可以通过对颅骨的扫描,然后在参照物的基础上根据软组织数据库的数据,将颅骨上的软组织“贴”回去。“然后再参考体质人类学的年龄、性别等信息,将DNA推测的色素沉积信息如肤色、瞳孔颜色、毛发颜色等再‘贴’一遍,最终完成个体复原。”文少卿表示,他们这次烈士研究实践更准确的描述是“法医考古”。
对于骸骨复原的条件,他表示,针对有参照物复原的情况,基本要求就是面颅骨要基本完整,如果仅有脑颅骨,对于复原的意义就不大;此外,如果只有面颅骨的一部分骨头,就需要采用镜像法将另一边的面部也“对称”过去。“至少要有整个面部的一半,这也是最低要求,如果连一半都没有,复原就不会太准确了。”
为烈士建立“档案”
看到他们的“群体影像”
从2015年至2018年,文少卿团队与多位田野考古学者合作,共收集了8个遗址的500多具“疑似”烈士遗骸样本,除了中国远征军的密支那战役,还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2019年至今,该团队又收集了两个战争遗址的遗骸样本,一个是河南荥阳的一处遗址,另一个就是此次的山西吕梁南村遗址。近9年时间里,团队共收集了1000多具“疑似”烈士遗骸样本。“很多时候都是与兄弟单位合作的,在他们完成了发掘工作后我们再带领团队过去取样回来,我们实验室就负责做DNA这部分。”
文少卿说,今年山西吕梁的研究与过往不同的是,从墓地发掘到烈士面部复原再到DNA提取后做同位素研究,他们将“DNA寻亲”这一单一目标拓展为一个综合研究,实际上可以看到多个研究方向在交叉融合,产生的成果也比较丰富。“我们做这件事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希望通过DNA技术锁定烈士的身份,为其找到亲人;第二个目的则是希望能通过体质人类学和病理学的方法,再加上同位素研究和DNA的研究,几个方法一起能还原烈士生前的生活和经历。”
文少卿表示,团队希望除了提供“形象档案”外,还能够为烈士们提供一份“生活档案”,包括他们的个体生活史,曾经患过的疾病以及体质特征等。“在有了足够多烈士的‘档案’后,就能够看到他们的‘群体影像’,这是非常重要的。”
“判定”烈士营养状况
同位素分析印证更多经历
“体质人类学可以确定烈士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病理情况等,在了解基本情况后又可以‘往前走一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推测烈士的死因。”文少卿介绍,如通过烈士遗骸的牙釉质发育不全、眶上筛孔等特征可以“告诉”人们,某位烈士的营养状况不太好甚至有些贫血;又比如留在颅骨上的一些弹孔,可以通过弹孔的方向,判定烈士中弹的位置;而通过烈士伤口愈合的程度,包括一些骨折损伤的愈合程度,能判定他的围死亡期。“比如可以看到烈士受伤后大概还生存了多久,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数据。”
文少卿告诉记者,在研究烈士遗骸过程中,他发现16岁到18岁的个体很多都患有退行性疾病。“退行性疾病大多出现在中老年人群中,比如年纪大了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而出现的关节类疾病,但这些烈士的实际年龄却不到18岁,可见当时他们的营养状态不大好,工作强度又很大,身体出现了未老先衰的情况。”
此外他介绍,根据碳氮同位素的研究,通过分析氮值可以发现烈士当年肉类和奶制品的摄入,“他们的氮值甚至比一些素食者还要低。”文少卿说,而根据C3、C4类植物的分析,了解到烈士们的碳值分布比较广。“这说明他们是吃‘百家饭’的,有什么东西吃就吃什么。”他还表示,继续研究又会发现碳值中C4是摄入植物的主体,主要就是小米。
他还举例,M21号个体是唯一一个在山西吕梁的战争遗址中出现印章的烈士,除了玉质印章外,还有一个玉制的烟斗,再通过同位素的相关数值研究,就更加能够推测他的经历了。“他小时候生活应该还不错,氮值相对好一些,再通过肋骨反映最后三年的情况,可以看到他可能作为军官,也同样和战士们在一个锅里吃饭,最后壮烈牺牲在战场上。”文少卿表示,数据是不会说谎的,通过这些数据的共同交叉,可以看到一名烈士身上的很多经历。
多学科数据交叉验证
“小人物大英雄”更能引起世界共鸣
“烈士寻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定他们的最终身份。” 文少卿说,只有在确认了最终身份后,遗骸才能从“疑似”烈士成为真正的烈士。
而据了解,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通过分析锶同位素来研究古人类的迁移。“像这次我们发现有7个个体应该并非山西当地人,有的来自南方,有的来自东北。”文少卿说,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战士也会随着部队流动,并不一定都是来自某个地区,这对于帮烈士寻亲也有一定的导向性。“当然DNA数据也可以推测其地理来源。”
作为一名“80后”,文少卿坦言,我们这一代所了解到的战争主要是来自课本上的一些资料记载,这可能会让战争有些“抽象化”,对于战争的实际感触还是有些距离;而团队通过多学科交叉验证,将这些鲜活的数据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会比较有冲击感,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数据了解到生命在战争面前的脆弱。
文少卿回忆,今年9月底,“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志和堂正式开展。他们利用3D打印技术将在山西吕梁发掘的烈士墓地“放置”在展厅的中央,直观呈现在所有观众面前。展览期间许多学生和市民自发在这块“3D墓地”上献上菊花,缅怀先烈。
“我当时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我的爷爷去了朝鲜战场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当战争发生,我还是会和祖辈们一样再次奔赴战场。这让我非常感动。”文少卿表示,通过科技手段呈现先烈的故事,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理解先烈们的爱国情怀。
此外,他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用科技手段产生的数据来讲述这些在战争中挺身而出的“小人物大英雄”,更利于中国故事的传播,也更能引起全世界的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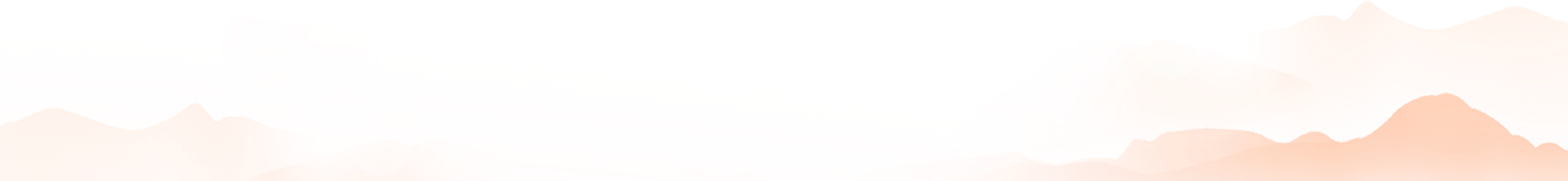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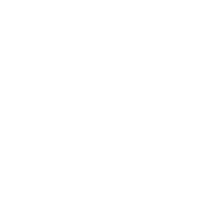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