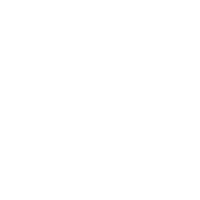菰,即茭白。
总在入夏时节,水水的陂南,总会呈现出她最柔媚的一面,荻、芦、蒲、菰、菱、萍、箬、蓼……,雨落生姿,水意葱茏。
菰生于野,见水生根,依水而长,修长、碧翠、温婉,宛如从泛黄的《诗经》里走出的一群如玉佳人,水,成了她们的温柔之乡。虽然,离端午还有一箭之遥,可故里早已潮润、迷濛、碧透。
一寸雨水一寸青,在这里,菰与雨始终联为一体。春来,在淤泥里埋藏了一冬的洁白的菰根,在雨水的滋润下,慢慢苏醒了,开始了恣意疯长,从最初娇若婴儿拇指的初芽,渐长为薄如脂玉的嫩叶,最后出落成绿汁丰沛、通体翡翠的水生植物——雨水,成就了菰的俊秀脱俗;菰,定格了故园的独有韵致。
雨季,隔着珠帘,远眺野菰,会产生一种无法言语的凄美。倘若,一定要用国画技法来表达,我以为,应运用湿染,以细软的羊毫饱浸清水,用花青蘸石绿,略染一点儿藤黄,尽可畅快淋漓,大胆落笔,尽情写意。
有时,并不需要看,只须静听,聆听那忽远又忽近的雨打菰叶的音律,慢慢地,你会感到有一丝丝绿意笼罩你的全身,有一种水岸的清凉让你情不自禁地打一个幸福的冷噤,惊喜地体味到“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的宋时意境。
倘若还不尽意,不如撑一把油纸伞吧,去访一座古桥,绿波里,桥影边,一丛野菰正在静静伫立,仿佛等了你千年;或去访一处园林,雨将一切隔在粉墙之外,那园仿佛此刻荒废了,不远处的池中,绿菰叶与红莲花沐浴在雨中,浓烈又凄楚;实在不行,就坐一尾不系之舟,任由它漂泊在菰雨深处,“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暂别这喧嚣的尘世,在野水里捞取一片心灵的自由。
人近中年,我总是忍不住回首,怀想那一个霞映澄湖的黄昏。雨歇天青,彩虹初挂,天空仍飘荡着银色的雨丝,山空湖静里,只听见水珠从菰叶等水生植物叶间坠落的嘀嗒,水鸟们每一声清脆的欢啼,总会惊落一层叶上宿雨。
仿佛秧田引来了秧鸡,野水总会逗来乡间的一群野孩子,一个个赤着脚,无拘无束嬉笑打闹着,去水边采菰。雨水,将一株株野菰孕育得青春而丰满,眼尖的孩子一见到叶间有纺锤般大小的实体,就水花四溅地奔过去,“咯吱”一声,将它掰下。
剥开裹着的绿衣,只见里面的茭白,光洁、莹润、玲珑、淡青,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甜的香气。终究忍不住,脆脆地咬了一口,刹那间,一缕含有湖野清香的甜汁溢于唇齿,感觉那是湖乡最佳的美食。
迎着袅袅炊烟而归,将新摘的茭白一蔸儿递与母亲,不一会儿,只见一盘鲜香诱人的清炒茭白端上木桌,在清贫的年代,茭白仅添拌了香油、盐、醋、青椒、蒜泥,便能引得一家人食欲大开。难怪乎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那菰、那烟、那雨,那江南、那碧水、那天青,成了游子的我一生的守望……
(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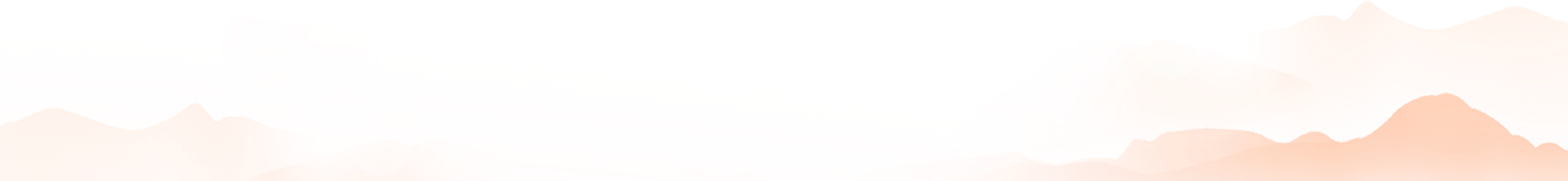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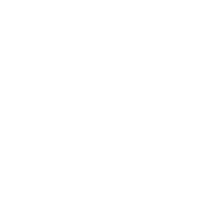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