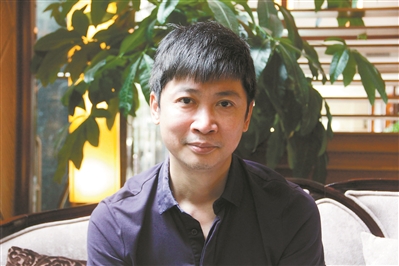“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近段时间,歌曲《孤勇者》成为大街小巷里小朋友们特有的“接头暗号”,其火爆程度连歌手陈奕迅本人都始料未及。他在微博发文调侃问道:“听说我出了首儿歌?”
对于像《孤勇者》这样的流行歌在儿童中受追捧的现象,有网友评论:“儿童歌曲传唱了几代人,主要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燕子》等老一辈音乐人创作的作品,新生的儿童歌曲少,而且难以引发共鸣。”对此,本报全媒体记者从儿童歌曲的创作、生产、传播等环节进行深度探访,了解目前国内儿童歌曲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为儿童歌曲的未来“寻路”。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除署名外)
“儿歌爷爷”吴颂今:
儿歌新作其实不少,缺的是宣传推广
在荔湾湖公园里有一个“颂今音乐空间”,炎炎夏日,总有游客和路人会不期而遇进入这个“网红”打卡空间。往往直到参观完,大家才发现这里的主人居然是被誉为“儿歌爷爷”的音乐家吴颂今,然后纷纷掏出手机要求合影。
今年76岁的吴颂今是国家一级词曲作家、高级编辑、著名儿童音乐家。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广州组建的“小蓓蕾组合”闻名全国歌坛。这个儿童课余歌唱团队由嗓音条件好、歌唱水平高的小歌手组成。被称为“甜歌皇后”的杨钰莹就曾是“小蓓蕾组合”的第一代成员。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如今各大商场超市门口摇摇车里播放的这首幼儿歌曲,就是吴颂今创作的。
“也许是职业惯性,我现在的音乐创作一直没停,不断有儿歌新作推出。”吴颂今边说边掏出手机点开自己的多个自媒体账号,里面上传的作品中,记者发现儿童歌曲占有不小的比例,仅在某一个短视频平台上他发布的作品里就多达数百首。
吴颂今告诉记者,如今的儿童歌曲新作品其实并不少,但是却很少能进入到孩子和家长的视野当中。
“年轻一代的儿歌作者,除了需要有创作热情外,还要考虑付出与回报对等的问题,因此写儿歌的积极性无疑会受挫。”他举例说,如今在短视频风行的年代,自己不仅要创作出足够好的儿歌,而且还要掏钱找人为儿歌配上动漫视频,“一分钟制作费就要一两千元,一首歌至少也要五六千元了。”加上作词作曲、歌手演唱、音频录制等其他成本,一首新歌耗资都要一两万,而未来能否收回成本却是个问题。
“缺少宣传推广是儿歌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 吴颂今认为,现在网络上新歌发布的数量远高于上世纪,每天都有上万首上线,“因为歌曲创作录制与发布都没有门槛了”,有的创作者写歌不用懂乐理,只要能对着手机哼几句,再找人记下谱来,配上伴奏音乐,套上歌词随便一唱就发表了。“真正有质量的歌曲佳作就淹没在这成千上万首的‘口水歌’当中,儿童和家长们几乎不可能从中将它们找出来。”吴颂今说。
近年来,吴颂今在海内外举办过11场个人作品音乐会。出于对儿童音乐的重视,每一场音乐会上,他都会“夹带”演出几首儿歌作品,其中既有《小手拍拍》等经典儿歌,也有《手机爸爸》等儿歌新作。他希望通过演出推广,能引起大家对儿童音乐的重视,但还是很难达到预想效果。
作曲家邓伟标:
“分众时代”,儿歌也应允许多元化
作曲家邓伟标与记者分享了一段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邓伟标的女儿5岁那年由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发行了原创歌曲专辑《邓澈——好爸爸》,该专辑被随后某动漫公司相中,把专辑中的全部歌曲制作成儿童动漫MV,在公交、地铁上持续播放过两三年。但由于邓伟标出门主要都是自驾,他从来没在日常生活中听到或看到过女儿唱的歌,还是妻子和邻居告诉他才知道。 “对于每天去坐公交,偶然会看到这些视频的人来说,他们就知道这批歌。但对于我来说就是完全陌生的,尽管歌手是我女儿。”
又比如在她9岁那年,邓澈被广东星外星唱片公司相中,签约成为该公司演唱组合“零食娃娃”的成员,演唱了大批儿童歌曲,甚至在海心沙、中山纪念堂、星海音乐厅等各类大型演出场馆都演出过。在星海音乐厅的那场演出上,该组合演唱了由日本音乐人久石让作曲、邓伟标填中文词的《天空之城》,吸引了全场一千多名学生观众放声齐唱,而现场的成年观众则不知所以,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状。
邓伟标告诉记者:“大概从2000年之后,世界音乐便逐渐进入到‘分众时代’,再也没有一首歌能够像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那样风靡全球,如今无论是谁‘红到发紫’,总会有一大批人没有听过他的歌,或者是大家知道某个歌手的名字,却没听过他的歌,这并不奇怪。所以,我们不应该用曾经的单元时代的观念来衡量多元时代的事物。”邓伟标说,“如果人们能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儿歌发展,心态上也会平和很多。”
他认为,既然无论大人和小孩都处于这个多元的时代中,自然而然也会被不断“分众”,“比如有的幼儿园老师就喜欢教他们自己喜欢的歌,也不能说这不好,而且小孩也谈不上没有歌可唱。我女儿今年已经17岁了,可能看到5岁小朋友唱的儿歌照样会提出‘不理解’的疑问。”邓伟标表示,毕竟她们曾经所处的时代不同,童年接触到的歌不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隔阂感”。
“我和词作家羽善是好朋友,他经常会发一些儿歌给我,我却很多都没听过,这就是一种‘隔阂感’。”邓伟标告诉记者,令他佩服的一点是,羽善两年间创作了3000多首儿歌,“他发过来了,我不打开听,过几天就忘了这件事,就会大喊‘没有儿歌了’,这其实也是外界普遍对儿歌存在的误解。”
词作家羽善:
儿歌创作有其“特殊性” 儿童自创歌词更能表达其内心
羽善是广州市流行音乐协会副主席、词作家,如今经营着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专门开展少儿流行音乐的创作工作。
“儿歌创作的难点主要是歌词方面。”羽善介绍,由儿童自己创作的歌词更能够准确表达发自他们内心的想法。为了能够掌握儿歌歌词的创作,他专门总结了一套“创作法”,让儿童自己创作儿歌歌词。“一般情况下,歌词的1、2、4句是押韵的,第3句会有些高音儿童难以达到,为了创作更适合儿童传唱的歌曲,我们创作的儿歌歌词第3句也讲求押韵。”他认为,根据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有些涉及到爱情、社会现象的歌词,以及那些高音太高、音域太宽的旋律,都不应成为儿歌。
羽善表示,如今之所以会出现成人流行歌曲被当作“儿歌”传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方面的“引导”:一个是传播力的引导,流行歌曲的传播力明显是巨大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儿童;另外一个则是老师们在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上的引导,也同样会对儿童在选择歌曲方面产生影响。
“我们曾经做过一些试验,那些由儿童创作出来的很唯美的歌词,加上音乐学院老牌教授的谱曲,让儿童唱出来的时候却‘不是那么回事’。”羽善说,词是词,曲是曲,当词曲双方缺乏足够的沟通时,就很难做到词曲表达的一致性。
为此,他在全国范围内签约了300多名儿童艺术机构的音乐老师,让他们共同为儿歌作词作曲。“老师们很多都是公益性的,靠着情怀和对儿童音乐的喜爱进行创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每年的上线儿童歌曲数量达到了2000首左右。”羽善说。
“我认为最牛的一首儿歌,是所有人都会唱的《生日歌》,其旋律并不复杂,歌词更是非常简单,但依然传唱度很高。”羽善说,真正适合儿童的歌曲,是能够让孩子们唱出自信、唱出快乐、唱出想法的儿歌。
“如今通过大量儿童歌曲的创作,新创作的儿歌有了其‘独特性’。”羽善介绍说,如“诗词歌曲”“名城歌曲”等,都具有其时代和地域的特点。也正是由于儿童歌曲创作的数量足够大、涉及领域足够广,通过歌曲的版权运营,公司才有了一定回报。“我们现在倒不希望某首儿歌能够人人传唱,这样的话,每首儿歌的‘出口’端还都能够把握;要是到了人人传唱的情况,恐怕连版权诉讼的成本都把公司拖垮了。”
广东省音乐家协会顾问陈洁明:
儿歌既要与时代同行,也要与孩子产生“共鸣”
“孩子是互联网虚拟世界的‘原住民’,而大人却是虚拟世界的‘移民’,就很难真正获得‘原住民’的认可。” 广东省音乐家协会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陈洁明告诉记者,儿童歌曲入门很容易,技术方面比较简单,难的是与孩子产生“共鸣”,往往是大人模仿孩子的思维去想象创作,较难创作出好的儿童歌曲。
他举例说,如乔羽老师创作的儿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以及在上世纪跟随影视、动漫等火遍全国的儿歌《红星闪闪》《鲁冰花》《世上只有妈妈好》《蓝精灵》《喜羊羊》等,都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而从“千禧一代”到“Z世代”,都有着自己的童年歌曲,对于互联网虚拟世界也有着自己的认知。
陈洁明告诉记者,他曾经为一首儿童诗《妈妈,我很孤单》谱曲,诗作者正是一位小学生,诗中写到“妈妈呀妈妈,我很孤单,月亮月亮都升上来了,你怎么还要去上班。妈妈呀妈妈,我很孤单,我想让家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说话。” 陈洁明说:“这歌词就很有想象力,反映的是当时留守儿童真实的感受。”
谈到儿童歌曲的推广问题,陈洁明表示:“现在很多儿歌创作团队的做法,大多是找动漫、游戏、社交平台等做媒介,或将一批歌曲全部上线,先看哪一首歌有‘火’的潜质,然后再追加投入宣传推广费用,一般到了那时歌曲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推广宣传费用也会大大降低。”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陈洁明说,一首歌能够达到儿童喜欢传唱的程度,不但歌曲本身要好听,主题也要与时代同行,且推广也很重要,但这在目前不断“分众”的时代下并非易事。
星外星音乐总裁周小川:
企业难依靠自身推广儿歌 创作者应看到聆听者的“价值”
“现在大多数新的优质儿歌与那些‘XX神曲’相比是天生不带流量的,商业推广很难。” 星外星音乐总裁周小川认为,在如今大数据时代的算法机制下,儿童音乐的推广不单只是音乐公司的责任。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儿歌所面临的境地被周小川称之为“儿歌迷途”,儿歌被动地变成了“曲高和寡”的那一类作品。
他解释道,在以往,儿歌作品还有纸媒编辑以及专业电台或者电视节目的推荐;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在“流量为王”以及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优秀的儿歌作品是不会得到推荐的。相反,类似于“音乐裁缝式”手段创作的“XX神曲”却总能收获足够多的流量。
“企业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推广优秀的儿歌作品。”周小川举例说,在公司发行的几十种音乐类别里,儿歌是“没法获利”的。“为了让优秀的儿歌更好地推广,公司专门投资了一家子公司制作儿童音乐广播剧以及动画节目,但却面临重重困难。”他告诉记者,几百万元投进去了,四年多还都看不到回报。“当然,这只是一个企业的起落而已,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儿歌面临的困境。”
“作为企业想要做儿童歌曲,要闯过许多道坎。”周小川说,在流媒体时代,唱片公司的大多数作品只能按各音乐娱乐平台定下来的流量规则去计算版权收入,失去了对产品的定价权,推广儿童歌曲不但需要与各个平台合作,而且需要迎合不同平台的“规矩”,效果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所以他表示,唱片公司大多会通过自媒体运营进行儿歌推广,但是“太累了”。
“进行儿歌的推广不能是一时之举,但是作为私营企业来说,很难一直推广下去,投入产出比很难达到预期。”周小川建议,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作者,都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儿歌的创作当中,真正地为下一代不断推出好的作品;此外,对于“好儿歌”的评价也需要有一定的维度,只有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能形成“普遍”认可、清晰的标准和规则。
“好音乐都是相通的,好的儿歌是能真实反映儿童心境,创作者也是要抱有善意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歌曲依然是美的、能被接受和认可的。” 周小川告诉记者,从艺术性上来讲,好的儿歌也更加能够隽永流传。“从华语流行到网络歌曲时代,再到社交时代和独立音乐时代,直至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听众在‘不断分众’的推动下,儿歌创作者还是要坚守初心,看到聆听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