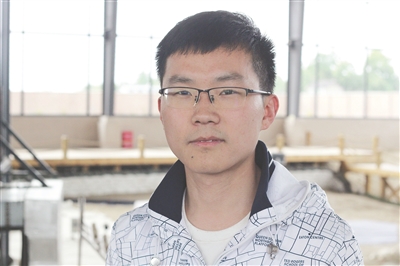今年同是26岁的许丹阳和杨镇,在三星堆遗址发掘中负责四号坑和三号坑的发掘工作,对于年轻的他们来讲,三星堆遗址已不是课本或材料中的只言片语,而是真实的感触和震撼。
无论是在四号坑内发现“令人惊喜”的陶器,还是在三号坑内发现国宝级的“顶尊跪坐人像”,都让他们更坚定地接过了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接力棒”,将自己的未来与三星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
位于三星堆博物馆两公里外的三星堆遗址,本是宁静的考古发掘现场,由于不少游客的“导航失误”——将三星堆遗址误认为是三星堆博物馆,遗址的门口的车辆也开始变得络绎不绝。
“这里能看到三星堆的文物?”一个游客询问遗址门口的保安。
“看不到,这里不能进,能看文物的是博物馆。”保安只好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解释道。
“考古”是可以一直坚守的职业
今年26岁的许丹阳是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负责人,来自河南洛阳的他,在去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加入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之中。
“我毕业于一个小县城的高中,当时对大学里的各个专业并没有什么很深的概念。”许丹阳回忆,当时觉得几个专业当中,考古似乎是与古代历史打交道的,应该还比较有意思,所以就报考考古专业。在本科毕业考研的专业选择中,“当时已经对考古挺感兴趣了,觉得能够作为一个职业去坚守,所以就继续报考考古。”
“我本身对古代历史挺感兴趣,通过考古可以直观地接触到古代留下的东西,感觉还是挺好的。”他说。
“来到三星堆遗址之前,对于三星堆遗址的了解大多是书本上的,而相关的资料也大多是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号、二号祭祀坑的情况。”许丹阳告诉记者,来了之后才进一步了解了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三星堆古城的城墙、大型宫殿性建筑等重要遗迹,以及三星堆遗址周边的同一时期的小型聚落,相关考古资料还是非常丰富的。
他介绍,从去年10月份开始发掘到现在,四号祭祀坑主要是经历了填土的发掘、灰烬层的发掘和器物的提取等工作,日常工作则包括具体的发掘清理、拍照、摄像、记录、测量、测绘等内容。
陶器的发现“令人惊喜”
“目前的发现在学术方面是有很大意义的。”许丹阳介绍,四号坑是有它的“特殊性”的,包括了特殊的埋藏方式以及特定的埋藏器物,目前来看,埋藏器物的分布、灰烬层的形态等是有一定的行为方式的,“这个坑是有特定的意义在里面的,有一定的规律在其中。”他告诉记者,已经提取的遗物、土样、碳样等各种样品是很丰富的。
“这个坑内埋藏了哪些动物、哪些植物,人工制品上有没有附着物残留等,这些都是后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展开了。”许丹阳说。
他介绍,从遗物的种类来讲,四号祭祀坑出土的象牙、铜器、金器、陶器、玉器、石器等都有。“象牙是比较直观的,因为后期灰烬覆盖,保存得也不太好,大约有40根。”其他的器类则相对不多,如出土的金器并不像五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那么震撼,有一些金带、饰片等,铜器也有几件体量不是特别巨大但造型比较奇特的,现在还在坑里,有待后续的清理提取。
他强调,陶器方面还是很令人惊喜的,在一般的遗址中,陶器很常见,但像这样的几个坑里出现陶器,那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和金器、象牙一起放进去的陶器,肯定就不是随便放进去的了。”他说,目前这些陶器都是打碎放进去的,是比象牙更早放入坑内,和其他的遗物一起放的,分布在坑内的四个角落和中间。而如果能够复原器形或者在陶器中提取一些残留,比如有机质,对于考古发掘的工作是意义重大的。
考古发掘没有硬性 “时间表”
“同时和不同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大范围来说,这几个坑都是属于三星堆文化,而且属于三星堆文化的偏晚阶段。”许丹阳介绍,可以说这几个坑属于同一文化阶段,但是具体而言,是不是在很短的阶段,甚至是一下子同时挖了这几个坑,目前还不容易给出肯定的答案,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检测、分析和研究。
他告诉记者,四号坑的测年数据已经发布,距今3200~3000年,接近三星堆文化的最晚期,相当于商代末年,或可晚到西周初年;而三号坑的年代可能和二号坑相去不远,但是否绝对同时还难以判断。他说,除非是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如二号坑有一件铜器是残的,三号坑也有一件铜器是残的,这两件铜器如果能够拼接起来,那就能确定这两个坑肯定是同时的。除此之外,无论是测年还是陶器比对,都只能大致判断。
“年代是判断坑的性质和作用必不可少的依据。如果年代问题不清楚,其他相关认识也会出现问题。”许丹阳说。
他告诉记者,每一个坑的流程大致都是一样的,从填土的清理,到把器物完全清理出来,从上到下按照叠压的层次一层一层清理,最后把器物提取完,再把坑清理干净,考古发掘就结束了。“目前并没有考古发掘的硬性时间表,考古是分轻重缓急的。”他说,如象牙是比较脆弱的,是有机物,而且失去了它原来的埋藏环境,当务之急是提取象牙,在提取了象牙之后,如果其他遗物能够在坑内还能够保存一段时间,还会要慢慢进行清理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坑内遗物边提取边保护
在三星堆祭祀区四号坑进行高精度扫描的同时,相邻的三号坑正由十数名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进行象牙的提取工作。
今年26岁的杨镇是三号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负责人,他介绍,目前在发掘舱内的人员包括考古发掘团队以及文物保护团队。“考古发掘人员有细致分工,除专门负责发掘的人员,还有专门负责采样、文字记录、摄影拍照、测量测绘等工作的人员。”杨镇说,文物保护人员主要负责出土遗物的现场及后续保护。“现在提取的就是编号为9的象牙,这根象牙的保存形态较好,分布相对独立,叠压关系相对简单,提交申请后,经专家讨论,符合提取的基本要求。”
在现场,记者看到在三号坑内铺盖了大量的毛巾和保鲜膜。杨镇介绍,现在清理出的遗物主要有象牙、青铜器、海贝、石器,铜器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发生氧化,而象牙如果不进行处理的话,会容易脱水干裂。因此,主要盖了毛巾的是象牙,盖了保鲜膜的是铜器,铜器主要是要进行保湿处理,尽量不要接触空气出现氧化,象牙的保护目的主要是为了不让它脱水。
他告诉记者,今年1月9日,由上海大学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三号坑进行发掘,持续两个月的时间,基本清理到了“器物层”,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提取。
坚持下去才会有“真正的发现”
家乡在四川内江的杨镇告诉记者,三星堆遗址在四川人的心中不仅仅是一个遗址,而且是一个文化或者精神符号,作为四川人看到这些出土的器物都会非常震撼,也深深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他进入了考古行业之后,感受到的则不只是震撼,因为这些发现还是探寻过去的一扇窗口。2020年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研究生毕业之后,杨镇就打算回到家乡工作,然后就来了三星堆遗址。
“当年可能是阴差阳错走到了考古这条路上,但也渐渐地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杨镇说,考古可以说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有时候发现不了会比较气馁,觉得付出了那么多却没有什么发现,但是坚持下去,或许就会不经意间等到“真正的发现”。
他告诉记者,目前发现的重器基本上都在三号坑内,其面积是14平方米,而有的坑面积也比较大,相信也将会有不亚于三号坑的发现。
新发现堪称国宝级
“三号坑埋藏的器物中,有此前见过的器物,也有没有见过的新发现。”杨镇说,见过的器物中有尊、罍、面具、人头像、神树以及眼形器等,比如此次发现的巨型铜面具,原来在二号坑中也有发现,但是二号坑那件是残的,这件目前来看是相对完整的;还有就是其中一件大口尊,是目前三星堆发现最大的铜尊,可能也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铜尊之一。
“这次最令人惊喜的发现是顶尊跪坐人像。” 杨镇介绍,该人像整体高1米多,堪称是国宝级的发现。另外,象牙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二号坑,二号坑的象牙数量官方数据是60余根,现在三号坑数量已经达到120多根了。“当然,这对提取和保护也增加了难度。” 杨镇说。
“如果选一件目前为止三号坑最令人震撼的器物,很多人可能会选择首次发现的顶尊跪坐人像,但是我会选巨型铜面具。”杨镇说,当时在发掘的时候只发现了大面具的侧面,连耳朵都没有露出来,“第一反应可能只是一个小残片。”但是当他们一点点清理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当初以为的那个小残片,其实是巨型铜面具左耳的连接部。
“我们当时看到这么大的耳朵,就在想会不会比博物馆出现的那件巨型铜面具还要大,或者就是那件面具的残缺部分?”杨镇回忆,当时的确有很多种猜测,如果这件面具是完整或相对完整的大面具,意义也是非常不一般的,“这也是我们除较早发现大口尊之后,清理填土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首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