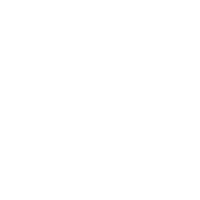翦翦东风里,在县城的南环路,向远方望去,看见的是大山旁逸斜出的一个“小枝丫”,无甚大名,俗称“南山”。
一悠腿,上了单车,今天就去访南山。
二三十里,烟村明河,树木萌芽。目之所及,万物处于冬寒中的黯淡神色渐渐被风揭去,嘴角松动,眼眉舒展,露出一种放松、快乐的表情。
我们把单车放在山脚下,迈动双脚,用行走去拜谒一座正在苏醒的山。
山清瘦着,肌肤还欠润泽,毛羽还不丰茂。背阴里一块块椭圆的残雪,已由清莹变为碱白,周边洇着一圈水渍。残雪的圆面日渐回收,我知道,它最后会变成一滴眼泪一样的水,在春风里无声消逝。
树也还瘦着,健硕,清朗,挺拔,还淘气,时不时舀一瓢风,泼洒到我身上,不尖锐,有点凉,是那种温柔的初春凉。一点点的凉,只在你外皮上肉虫一样爬过,再也钻不进肌肤里了,更别说侵入骨髓。悄悄的小变化,这就是节令的暗语吧。南山的微笑,正一缕缕晕开去;也许我们走过后,它就轻轻笑出声儿来。
草芽正在往外拱,有的攥着小小的拳头,像为自己加油鼓劲;有的尖尖的,像一枚针,楔入春风里;有的新芽,是一墩老绿从去年绿过来,不曾被冬日的大北风剜走,于是又老皮老脸地推送着自己的孩子芽芽,往更高处走。一片片草芽连起来看,像书法家的小楷,有骨有肉,有血气,有风神,字字都立着,伸胳膊踢腿儿,整齐端肃。
一座山的骚动,就从一根根草芽的拱动开始了。它们一点点钻进脚心,你会感觉到泥土的松动。一种坚硬的心意如何慢慢瓦解,慢慢返绿,你只有在初春的南山才能明白。
这时,我想打一个电话告诉谁,我在这里,你来吗?你若来,就在初春来吧,跟我一道感受这春风苏醒的南山。这里,草芽如此踌躇满志;大树,却稚童一样憨皮,这是一座山的法度与修为。此时,太阳蹿上了半空,阳光一晃一晃,照得我眯上了眼睛。我停住脚步,阳光也停住。站在我和阳光之间的,是一棵老树。我看出那是一棵有想法的枣树。它的树皮坚硬皴裂,裂成一片片甲骨;它的主干在光阴里慢腾腾生出数个分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静态的好像又是动态的,动态的又仿佛是凝固了。它的想法是几个世纪的沉淀,是一个个年轮互相磨合的结果,是一轮轮春风的唤醒。东风里,老树只待换新颜。
我走过去抚摸它,它立即用尖厉的触觉回我以微笑。是的,你不要以为春天的物事都是温柔的。那些有阅历的家伙,都是一脸严峻。其实,粗粝也是一种春天。
无数的大树小树,都在攒劲儿萌发。春意撬开枝干上龟裂的树皮,用力地涨啊涨,不消多长时间,绿色就会涂满半空。深深浅浅的绿被南山高高举起,劈开一条通往四季轮回的大道。
大树摇曳,不慕其高;小草萌芽,不欺其小。一山的生灵,都在攒劲。南山不厚此薄彼,你要一小摊儿泥土立足,好,给你;他要一片天空招摇,好,只要你有钻云穿风的高度。山无言,和谐又平衡。
其实,南山,多么繁忙。它的身体里,有多少正在苏醒的种子,有多少正在蓬勃的花朵,还有多少梦想和愿望。初春,它呈现的,只是那么幽微的一小部分,它们都不是山的本身。
你若走累了,那干脆席地坐下,吹吹风。你坐下去的地方,说不定有几粒种子正在萌生发芽之心;而你也正以种子的方式,融入南山。你跟山一道滋长,发荣,看它从无到简再到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奇异地变出万物花开。此时,你是南山一个核儿,像一粒从脚心钻到身体里的春天,仔细拆开自我,迎候每一个绒绒的日子。
(米丽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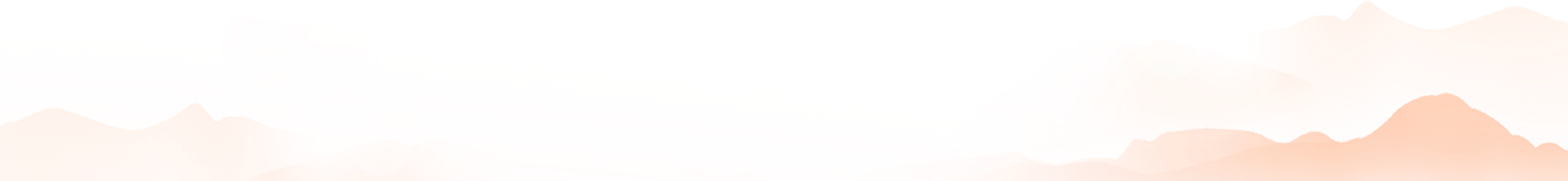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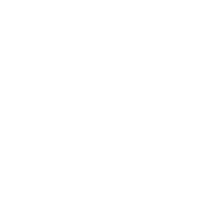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