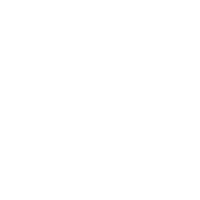一只鹅嘎嘎嘎叫着,摇摇晃晃走过小镇的狭长街道,大约需要23分钟。
这只鹅,是老郭养的。4年前,老郭和妻子来到小镇居住,过上了他想要的慢生活。老郭对妻子说,就养几只鹅吧。鹅被老郭养得憨实白胖,老郭有时候就跟随着一只鹅的步履,去小镇街巷散步。小镇的居民,都认识老郭家的鹅了。老郭家养的鹅,像老郭一样,喜欢散步时东瞅瞅西望望,一副好奇的样子。
老郭在城市郊外有宽敞的别墅,那年秋天,老郭突然对小镇生活着迷,来到离城12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居住。老郭的幺姑在小镇附近一个村子居住,93岁的幺姑鹤发童颜。幺姑家的表弟在镇上有一套闲置的青砖小院,多年没人打理,早已蛛网密布,但经过老郭和妻子收拾装扮,小院让镇上人也喜欢上了,他们常到院子里来坐一坐,同老郭闲聊,其实也是打探他来小镇居住的缘由。
起初,在小镇街坊的传说里,老郭是一个落魄老板,为了逃债才躲进小镇的。但后来小镇人发现,看望老郭的客人纷至沓来,他们都不是来催债的,是来院子里喝茶,雨天就在小院里听雨打芭蕉。老郭也豪爽仁义,常邀约小镇人到他家做客,一起做饭。
小镇上的居民,大多在小镇四周有土地,一年四季的新鲜瓜果蔬菜,几乎不要老郭去镇上买,他们一筐筐送来。有次我去老郭那里玩,我和老郭正在午睡,一个面如核桃的老人扛着一个硕大冬瓜径自进门而来,他把沉甸甸的冬瓜放在地上说,刚在小镇后面地里摘的。老人说,这冬瓜狡猾,躲在草丛里长得这么大了还没被发现,要不是他进去割草,这冬瓜说不定就一直在那里老去了。当天晚上,老郭夫妇就用这冬瓜在柴火灶里炖肉招待我,还喊了小镇上的几个人来陪我。那天晚上,老郭为我铺好了干净床被,他在床边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兄弟,你是能够与我终老的朋友,这里的门,随时为你打开。”
前年春上,老郭接下一个小镇居民送给他的几分坡地,老郭就学着做上了一个农人,在二十四节气流转的天光雨露里种上了红薯、洋芋、茄子、西红柿、丝瓜、豇豆、四季豆、芫荽、莴笋、白菜、葱蒜……或许老郭祖上都是种粮人,农人的基因还埋在他骨子里,他很快成了一个种地能手。小镇不远处有一个养殖户,那人对老郭说,猪粪给你留着当有机肥。有次我去小镇,看见老郭在田间小径担着一挑猪粪晃晃悠悠地迈着步子,那姿势与一个乡间老农完全没啥两样。老郭的菜地里,这些腾着大地之气的蔬菜瓜果,也常常成为我和友人们在城中的盘中餐。而今,我和几个老友在微信里对老郭的备注就是“小镇菜农”。
老郭的小镇,是联结我与乡土大地的脐带,让我在城市里涌动着对小镇的亲切乡愁。小镇而今还沿袭着每隔3天的赶集民俗,赶集那天,平时清寂小镇腾起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四面八方的乡人们摩肩接踵聚拢小镇,交易农产品或买生产生活用品,那些卖了农产品的乡人,大多要在镇上馆子里炒上一盘菜,喝上一杯老酒,微醺着才离开小镇。小镇上有一家土菜馆,厨子以前是一个屠夫,浓黑眉毛上扬,带着一股“杀气”,两年前开上这家小馆子后,我发现他眉毛已经软软地耷拉下来,面相也显得和善起来。这厨子确实烧得一手好土菜,都是本土乡野里的食材,肉也是喂养的土猪、土羊、土鸡、土鸭,吃着那肉,香浓黏嘴。厨子有一道土菜,叫高粱粑煎土腊肉,实在是我的最爱。寂静乡野,种高粱的乡人已差不多绝迹,但这厨子在小镇后面山坡上,种了一片红彤彤的高粱,秋天,还没等到霜降,沉甸甸的红高粱在风中摇摆,我去高粱地里转悠,如一个醉酒的人那样兴奋。
离这小镇两公里外,有一片黑压压如浓云堆积的松柏树林,那里有个山岩叫鹿鸣垭,据小镇老人所说,祖辈们常听见那里有嗷嗷鹿鸣传来。鹿鸣垭里有一个巨大山洞,冬暖夏凉。去年秋天,我在那山洞里心无旁骛地读完了两部心仪已久的长篇小说,这与在城中磨磨蹭蹭的阅读习惯是大不同的。我一个人在山洞里掩卷之余,望着那如老僧入定的苍松翠柏,感觉自己浮躁翻滚的心,有着深山的笃定安稳。
前不久去小镇看望老郭,离开时,他送我出门,青石街面上,两只白鹅一左一右慢悠悠走着为我带路。我蹲下身,像老朋友一样跟两只鹅打着招呼。我在说,你们好啊,鹅,鹅,鹅。
(李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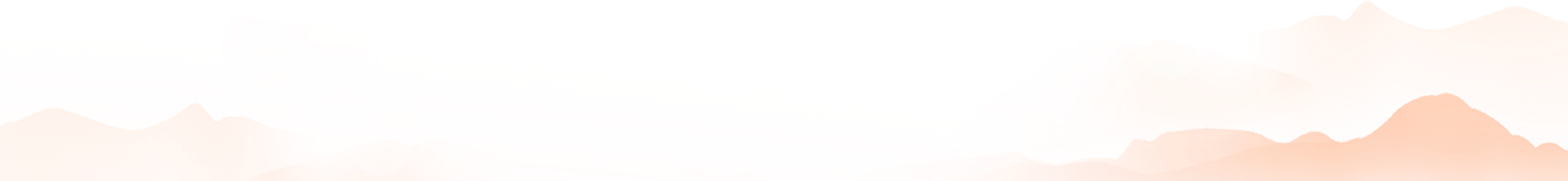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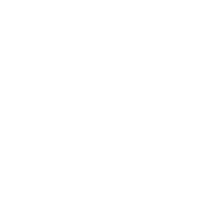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