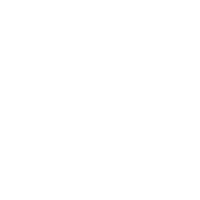老屋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高过屋顶,有碗口粗,郁郁葱葱。树身笔直,粗糙的树皮疙疙瘩瘩,开裂成一块块的,形似小瓦片,又似鳄鱼皮,横七竖八的细纹遍布其间,就像父亲冬天干活的双手。母亲说,树比她先到这个家。
我的童年很枯燥,除了和小伙伴在街头巷尾东奔西跑之外,没有什么玩具,倒是这棵柿子树带给我许多乐趣。春天来了,柿子树开花了,翠绿的叶子下,一口口浅黄色的金钟悬在枝头。春雨随风潜入夜,早上柿子树下便铺了一地黄花。我和姐姐们用细线把柿子花穿起来,戴在脖子上,那就是黄金项链了。
我时常抬头望树,急切地盼望着柿子快长大,天天看,总不见柿子有明显变化。青翠的柿子结得很密,每天都会有扁圆形的小柿子从树上落下,拣起核桃大小的落果,放至窗台,一两周后,绿果发青变软,咬一口,并不苦涩,倒有几分酸甜。
“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在等待中,柿子一天天长大,由绿变黄,有鸡蛋大小。父亲摘下几篮子黄灿灿的柿子。我偷着咬一口,又硬又涩。母亲盛一大铁盆温水,把柿子泡在里面,每天换两次温水,说这是“拔柿子”,去涩变甜,两天后就能吃。我哪里能等得及,总忍不住要偷着咬一口,浪费了不少好柿子。
“露脆秋梨白,霜含柿子鲜。”霜降过后,秋风拂过,柿子树叶纷纷飘落,留下一颗颗鲜红的柿子挂满枝头。远远望去,柿子树上仿佛挂满了一盏盏小红灯笼,甚是美观。这时候,常有乌鸦“呱呱”叫着啄食软柿子。我有事做了,可以光明正大地用弹弓打乌鸦。等到满树的柿子变成一片红霞的时候,父亲爬上树,用长竹竿把柿子打下来,一层层摆放在大木盆里,等着它们变软。我挑软柿子剥了皮吸着吃,香甜爽口,那就是我儿时幸福的味道。
软柿子太多吃不了,母亲把它们捣烂,和面粉拌在一起擀成圆饼,烙柿子饼给家人吃。那可是有钱难买的美味点心。
一些软柿子放坏了不能吃,母亲舍不得扔掉,把他们放在大瓦盆里酿成柿子醋,酸酸甜甜的,既是调料,又是我童年唯一的饮料。
后来,父亲盖了新房要搬家,和母亲商量要卖柿子树。我舍不得,哭着央求父母把柿子树移栽到新宅院子。父亲没有答应,说古树参天很难移栽成活。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柿子树没了,树坑已填平。我伏在地上伤心地哭了。
时至深秋,又到了一年吃柿子的好时节。思念故去的父母,甜柿子竟吃出了几分苦涩。我不禁想起老屋那棵柿子树,那里曾经有我美好的童年回忆,还有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快乐岁月。时光若能倒流,我还是想吃父亲摘的软柿子、母亲烙的柿子饼,还想喝一口母亲酿的柿子醋。
(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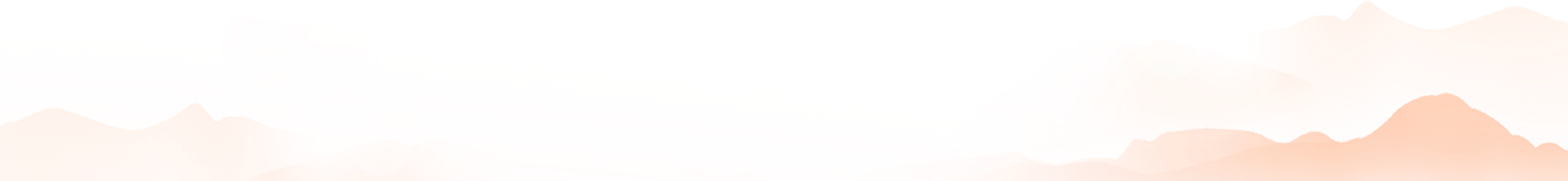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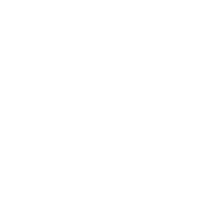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