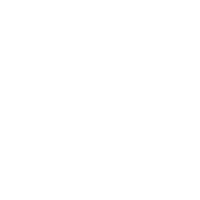三月间去郊野踏青,路过山坡旁一农家小院,院篱沿边围满芳草,萋萋然没有辜负我的眼光。那草叶薄片不带芒齿,细嫩柔软,风吹两边摇曳,互不缠绞。一蔸蔸一行行守规守矩,认真地向上生长,跟我家乡栽种的喂鱼的苏丹草长得一模一样。那一刻,我内心十分笃定:这就是鱼吃的草。像韭菜,割了一茬又发一茬,直到冬天鱼歇食沉潜水底,草叶才枯萎,然后化作泥土护根蔸,来年春又蓬蓬。
这个初秋,我再次来到那户农家小院边看草,它们还在原地未动,只是样貌大变了。宽扁的绿草叶丛间,开满了小百合状的金灿花,还有一些含苞待放的,像一根根彩色小蜡笔棒,有的青有的黄,有的黄绿夹橙红,暖色系鲜丽夺目。我惊喜不已:那草竟然是萱草呀,那花当然是忘忧花无疑啦。
看来真正辨识清楚一件物事,不能单凭短暂的眼光测定,还需要时光的积淀。
想起开学季,一位长得如忘忧花般好看的女生,忽然到访叫我老师,见我神情有点错愕,她连忙自我介绍:“您忘了?我就是您说的那个左边有书右边有剑、文武双全的‘刘’学生。”能说会道的她,一脸阳光自信。刚考上博士,从广州去北京读书,辗转经过老家,顺道过来看看。虽然微信常发问候,不见已有三秋。她不再是十多年前那个羞怯不语的小女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已能为我师了。时光真实,改变眼光。
时光倒回她初来学书法时,才齐我胸腹高。盖一头“西瓜皮”短发,刘海浓茂,老是低着头,使得我很少见到她的眉眼。她静静地躲在角落,写完又捂住那些颤抖游移的“黑草海带”线条,不给我看。当时我还年轻,眼光里闪现的,尽是一些早开的花儿带来的成就感。
那些早开的花儿,也很早飞走了。刘学生说她是笨鸟飞不起,留下来陪了我几个寒暑假。写久了写累了,她把笔一扔,也有想放弃的念头:“还是写得好丑!”我不爱说违心动听的话哄人,便给她讲一些零散的小故事,想着激发她的信心,更想着打发这枯燥乏味的上班时间。
《卖油翁》中的老翁,何以斜眼看十发八九中的陈康肃公射箭?“无他,但手熟尔。”刘学生拿起笔,她的手慢慢练熟了、练稳了。想必她的学业也是如此勤奋自律得来的。时光漫漫,眼光秒秒,以为不会开花的小草,长成了一棵开花结果的树。我本无心栽花插柳,却在时光悄然洗礼中,获得一段快乐的忘年之交情谊。
时光比眼光更会识人。后来我渐渐发现,聪明的孩子很容易接受一项新的技艺,但很快就会感到自满,而对此技艺失去兴趣并厌倦。因为快速的成功,终究是少了时间的磨砺,就像没有扎根的花束,只是一时耀眼。所以到最后,真正能成大事的,往往是那些起初看似平平的,甚至表象上有些笨拙的,他们静得心、耐得烦,忍受得寂寞时光。
时光里的坚持,是眼光中永恒闪烁的智慧。时光从不说谎,永远是眼光真心实意的好朋友。 (朱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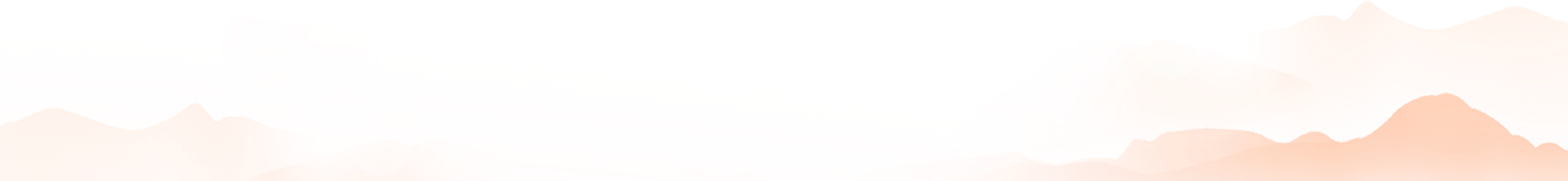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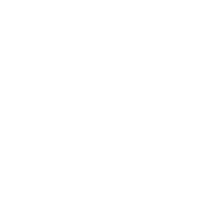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