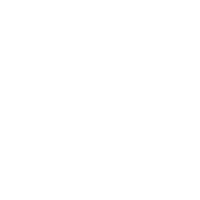春夏之交,天气阴晴不定。
周六上午,刚想出门,天色忽然变暗,少顷,雨嘈嘈切切落了下来,密密集集打在玻璃窗上,痕迹斑驳,映得窗外街景支离虚幻。
我喜欢下雨天。小时候,家住在半山腰,下雨天,总爱闲坐在二楼的小窗前,抱膝看雨。看雨落在花瓣上,看雨落在竹叶尖,看雨落在松林里,看雨落在山坳中……梨花带雨,有雨,花比平时多了韵致;竹叶青青,有雨,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就连松树,下雨天,也陡然多了些沧桑感,像父亲,挺拔、冷静、城府高深;山,越发秀丽,越发空蒙,越发神秘,皆因有雨,才有“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
2016年初夏,去东莞可园游玩,忽遇大雨,一个人蹿到可园的一间小阁楼里躲雨。窗户边,一丛芭蕉丰茂葳蕤,蕉叶青翠可人,团团新绿,映照屋内,给人一种清凉之感。雨打在芭蕉叶上,开始是小雨,入耳有宋词风味,滴滴答答,细碎咏叹,充满写意之美;后来,雨点慢慢变大,声响越来越密,像白居易的《琵琶行》,如锣鼓、似丝竹、像钟鸣……给人无穷的想象和无尽的乐趣。
傍晚,雨住了,从可园出来,忽然想起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在《看见》序言里提及的一则轶事。学生拜访朱光潜,欲替老师打扫院里的落叶,朱光潜拦阻道:“我等了好久才积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里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是啊,雨声真美,小楼一夜听雨声,有雨,心境就美,何必去管它第二天有没有人卖花呢。
后来,读苏轼的《喜雨亭记》,那是他26岁时所作,初出茅庐的他来到凤翔县做“签判”,满眼都是政治抱负,他将府衙后一块荒废的空地,改造成了一个小花园,又在花园中心土丘上修了座可观赏景色的亭子。修亭时,当地干旱严重,苏轼被派往太白山求雨。求雨归来后,他写疏奏给皇帝,请求将太白峰龙神的爵位由“侯”重新改回为“公”(因为唐代就封“公”),因为他“怀疑”是龙神降了级,闹情绪,不下雨。皇帝还真的信了他,降旨改封为“公”。无巧不成书,过了些日子,阴云密布,雷声轰轰,下了一场透雨。百姓欢呼雀跃,恰在此时,园亭完工,双喜临门,众人前往庆贺,苏轼遂给小亭取名“喜雨亭”。苏轼的抱负,如雨润万物,雨声里,他最听不得黎民疾苦。
前几日,重读《幽梦影》,当读到“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时,心里忽然生出个小小的愿望,要是能有个小院,也想像苏轼一样造一座喜雨亭,亭旁种上一丛芭蕉,邀雨,邀蝉,邀明月。
(刘新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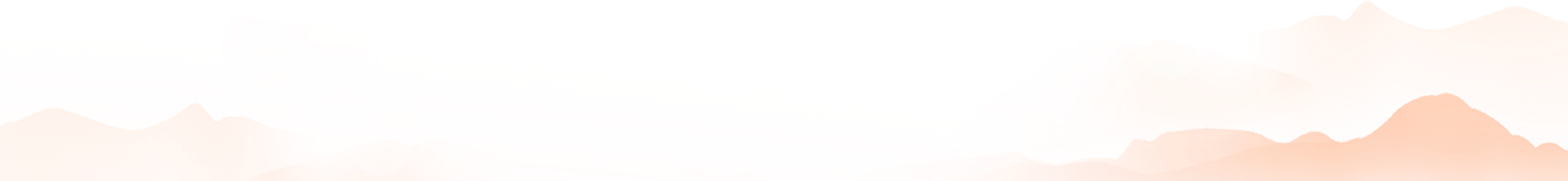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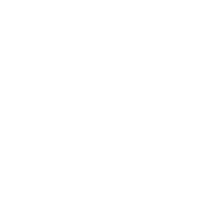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